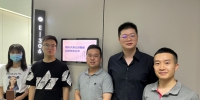年幼童工被遣送回大凉山 抱怨称“太倒霉了”
大凉山的孩子三四岁就开始干捡柴等家务活
则日哈的4个年幼孙辈在吸毒身亡的父亲遗像前
大孩子带小孩子,在当地是传统
孙子作日的同学们手关节都冻得变形了
刚被遣送回来的吉曲阿牛说,他们要不了多久就会再次出外打工
“就在深圳一批年幼童工被遣送回大凉山后不久,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警方近期出动大批警力,在路上又拦截了35名正欲外出打工的少年。这些被拦截的十几岁少年为此十分沮丧,准备接孩子回家的家长们脸上也露出了不满和不屑:“出去打工至少能吃饱饭 ,为什么不让出去?” 理由听上去简单粗暴。但接下来几天,记者深入大凉山,所见所闻令人不禁心酸。”
16岁的“老工人”
似乎是造物主最纠结的一次创作:大凉山,一个常与贫穷、落后、苦痛等字眼相连的名字,同时又是一个与令世人骄傲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紧紧相连的名字。最近,这里爆出儿童大量外出打工被遣返的消息,让这里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追踪着被遣返童工们的足迹,记者来到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凉山州)。
1月8日中午,在从凉山州西昌开往昭觉县的长途客车上,记者认识了刚刚被广东省劳动部门遣送回来的一名童工,彝族女孩吉曲阿牛。很显然,她一点也不想回到大凉山。
“我都16岁了,为什么也要把我送回家?”吉曲阿牛似乎怨气十足。“我太倒霉了,正好被抓到。还有许多年龄比我还小的人,藏起来了怎么不说?”
吉曲阿牛和她的一群小伙伴是去年12月8日到达广东东莞打工的。吉曲阿牛是昭觉县城北乡人 ,在这之前,她已经在深圳有过3年的打工经历,在一同外出打工的小伙伴中,应该属于“老工人”了。孩子们并不知道小小年龄外出打工违法,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1岁,最大的也才16岁。
孩子们是由中间人介绍并带出去打工的,他们在东莞一家电子工厂从事手机摄像头的拼装焊接工作,每人每天要焊接1000个。一条电动输送带把所有人分成两边,只要输送带还在走动,人就不能停下来,几乎每天平均工作12个小时以上,除了午餐时休息半个小时以外,中途不允许说话、看手机发短信,连上厕所或喝水时间过长都会被罚,每次罚款60元。工资每小时仅12元,还要被介绍他们来打工的中间人抽成3元。
“我们不懂有没有加班费、过节费之类的,中间人给多少就拿多少。”吉曲阿牛说。
尽管外出打工的日子很艰苦、要求很苛刻,但吉曲阿牛却说“回家住几天就要再找地方去打工”,因为外面打工的日子再艰苦,也总比在家里受穷受苦要好得多,“有能吃饱饭的地方也就满足了,何况还能给家里带来收入”。
妹妹供养哥哥,这是传统
走在凉山州偏僻的县乡,要找到曾经外出打工的少年并不难,有人告诉记者一个十分容易辨别的方法:身着奇装异服、头顶造型夸张的黄发,准就是他们了。这在当地就跟出去“留学”归来一样,会让山里其他小伙伴投去羡慕的目光。
只有大人或者大点的孩子,才懂得他们背后的牺牲。
17岁的昭觉中学高二学生孙子作日也懂得。
孙子作日的妹妹12岁起就外出打工 ,每月按时汇款回家,才得以让他升入高中读书的。
“妹妹的月工资是2300元,每个月都要给家中邮寄1000元,这些钱是全家人的生活来源,包括我的学费在内。”身着一件单薄红衣的孙子作日,哈着气把双手放在嘴边暖和了许久。他告诉记者,身上的这件红色衣服也是妹妹给钱买的。他很感念妹妹的好。“牺牲她给家庭做贡献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孙子作日羞愧地说。
在大凉山深处的村庄,靠10多岁的少女外出打工挣钱养活一家人的不是少数。昭觉县达洛乡的达洛村情况也是如此。村里51岁的木匠文古九都早年干得一手好活,后来由于干活时身体受伤就不能再出力了,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15岁的女儿文古果果身上。
“文古果果在山东威海一家玩具厂打工,今年是她到山东打工的第二个年头。”妈妈指着墙上张贴着的文古果果2009年上小学时获得的“三好学生”奖状,自豪而又无奈地说:“果果学习很好,从小就很听话,让她外出打工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家里实在是太穷了。她每个月邮寄回家的1000块钱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哥哥文古你格上学读书的钱也是妹妹挣的。”
在这偏远的山区,当地人说女孩儿未出嫁前都会被家人送出去打工 。早点送出去,就能多挣几年钱,这是许多人家的“传统”。
毒品吞噬着父母
凉山彝族是彝族中最大的一个支系,人口约有200多万,分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及其周边地区。大凉山地区如今吸毒、贩毒与艾滋病问题泛滥,由此导致的大量人口死亡、伤残、入狱以及家庭分崩离析,也使这里的儿童生存境况恶化。这也是孩子们外出打工的主因之一。
在昭觉县的另一个村庄瓦古村,记者就见到了不少因父母吸毒而失去依靠的孩子。67岁的则日哈老人的孙子就是这样的情况。
正午时分,记者走进则日哈老人家时,阴暗的屋子中间正点着一堆烧着热水的火,在通红的火堆旁,有8双小小的手探出来烤着火。这是则日哈8个年幼的孙子孙女。他们最大的9岁、最小的才4岁。不一会儿,午饭抬上来了,这些穿着破旧的孩子每人抓了一个凉洋芋,娴熟地剥掉洋芋皮,蘸着一个小盆里的油炒辣椒末吃。他们的午饭几乎天天如此。
中午的太阳光透过房顶并不严实的缝隙,照射到靠近门口墙上挂着的一个相框上。相框里的照片上有个嘴上叼着香烟的年轻人,低头正在逗一个年幼的孩子。“这是我的儿子,因为吸毒已经死了,小孩子就是屋里8个孩子中的一个。”则日哈老人眼神中充满忧郁和无奈,“我这一家十几口人,居然一个能干活的劳力也没有。”
则日哈共有5个孩子,其中两个儿子和1个女儿先后因吸毒和艾滋病等问题,夫妻双双去世,共留下了9个孙辈由他抚养。“其中1个大点的上山捡柴未回,其余8个孩子留在家中,照看一头牛、两头猪,还有几只鸡。”则日哈每年有600元的低保,健在的两个儿女离开村子在县城生活,很少回来。眼看着孙子、孙女渐渐长大,饭量也在日益增长,大家不可能一直就这样在家里耗着。“我准备让大些的孩子外出打工,一来能够自谋生路,二来也能贴补些家用。年纪小的希望能去读免所有费用的孤儿班,毕竟孩子是要学些知识的,不能像他们的父亲那样。”则日哈对记者说。
从放羊女,到生放羊娃的女人
女生阿星全名曲比阿星,14岁,凉山州金阳县人,父亲早亡,母亲改嫁,阿星只能靠自己的坚持还有爱心人士的资助一步一步向前走。
曲比阿星8岁的时候,父亲为挣钱出门打工,在一场意外车祸中不幸丧生,生活从此变得无比艰难,对一个凉山彝族的女孩子来说,就更加没得选择。按常规的生存之道,阿星将成为一个放羊女孩儿,然后变成一个生放羊娃的女人。果然,一年后,阿星的亲戚占有了本属于阿星的抚养费,她辍学放了一年的羊。阿星说她那时甚至希望像其他姑娘一样早点嫁人,结束这无聊而危险的生活。
那年,她才9岁。
又过了一年,曲比阿星被一个好心的叔叔偷偷带到西昌,送进现在的学校。这时,一扇门在她的眼前徐徐打开了,她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城市,知道了除彝族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别的民族,懂得了生活还可以有无穷的乐趣。念完七年级上学期的那个寒假,阿星的妈妈改嫁了。按照彝族的传统,改嫁以后的妈妈是不能再管孩子的。亲戚们因为阿星是个姑娘显得对她非常“关心”,因为在娶亲困难的大凉山,嫁女可以得到很高的彩礼钱。阿星几乎是有些漠然地对记者说,亲戚们以很高的价钱将她许配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男人,本来就要嫁过去了,但是那家人家一次也付不起如此高昂的彩礼钱 ,只能先付首付,每年再付分期……
那年,曲比阿星13岁。
“要么你们就不该让我知道山外的世界,要么就别让我再回去,我不能就这样嫁人……”亲友们今年把阿星抓回家里完婚,她又偷偷地逃回学校。校长得知阿星的遭遇后决定,只要阿星想读书,就由学校全额资助。后来,阿星才知道,她的亲戚们打电话给校长,要学校补偿逃婚的损失。到了寒暑假,阿星无处可去,只能待在学校里,值班的老师主动带她一起吃饭。校长为了让她有人照顾,给她认了个姐姐 ,尽可能给她提供一些帮助。有时候,阿星也会怀念那个家,可是她不敢回去,怕没有机会继续出来上学。
再过一年,阿星将从这所庇护了她3年的学校毕业,她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她想继续读高中甚至上大学,但这似乎遥遥无期。
贫穷,让她的人生一次次走到迷茫的十字路口。这就是一个普通凉山孩子的境况。
本组文并图/《半岛都市报》记者 刘延珉
新闻延伸
他们需要比遣返更有力的帮助
记者在昭觉县强制隔离戒毒所门外采访,不到半小时就看见先后有三辆鸣着警笛的警车出入,而门口就有许多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押进去的孩子。“在凉山州山区许多地方 ,小孩子都知道怎么吸毒,这是在家里耳濡目染的。”给记者当翻译的出租车司机拉祜说。
据了解,截至2009年初,凉山州发现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已突破万人。如今,在统计的感染者中 ,静脉吸毒者占一半以上,大量三十多岁的妇女又被自己吸毒的丈夫感染。昭觉县是毒品和艾滋病的重灾区之一。截至2007年10月,昭觉县的艾滋病感染者有2038人,孤儿总数为1181人,成为当地很大的隐患。
这些惊人的数字很尴尬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大凉山的贫困不仅仅是因为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当国道和高速公路已经通到了凉山州的时候,那些日渐增长的感染者和孤儿数字仍然触目惊心。
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帮助村民脱贫,或许这里的孩子仍然甘愿做童工,被一批批送往东部沿海的工厂……
事实证明,情况或许确实如此。在昭觉县城北乡古都村,记者以玩具厂亟需招工的企业主身份,通过当地的黑车司机联系上了一位可为企业介绍童工的中间人结火曲山。
结火曲山向记者保证,只要有需要,他可以很快帮忙找到足够多的10多岁的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