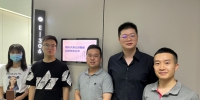新城乡:国家试验区农地流转调查
土地增值,农民权益,资本态度,发展羁绊,越来越能清晰判断这方土地上的样本效应
□本刊记者 张守帅 刘莉
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为标志,中国农村迎来新的历史拐点。
至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确立31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过半,中国面临“三农”新问题、新趋势。在此背景下,《决定》提出,“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
在成都农民看来,“土地流转”并不是新鲜词汇。数据显示,到2006年底,成都市流转土地面积即达153.78万亩,约占农用地总面积的14.04%,到2012年,成都市流转土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已达47.9%。
成都市农业部门曾结合经典案例,总结出7种农用地(非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包括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公司、土地银行、家庭适度规模经营、业主租赁经营、大园区+小业主、两股一改等,显现出基层探索的蓬勃活力。
按图索骥,记者在2013年岁末回访上述案例提及的成都双流、新津、温江、崇州、邛崃、彭州等区(市)县,所到之处印象深刻:
尊重农民选择权、建立合法转让权、保障土地财产权,推动了大规模流转的顺利实施;不同的模式探索,受地理区位、耕种模式、思想认知等因素影响较大;以设施农业、绿色有机农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是工商资本投入的主要方向。现代农业回报高,但不乏风险,部分企业风光难再,陷入经营困顿;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成功案例屈指可数;观光农业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匮乏,显示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进入深水区的艰辛与复杂。
农民“包租公”
和盛镇,地处温江城郊,以种植花卉苗木闻名,拥有西南最大的红枫林种植基地。“全镇已流转土地1.6万亩,占耕地面积70%以上。”镇“三农”办主任吴建说,农民间转包土地可追溯到10多年前。他清楚记得,2000年村民转包土地的租金为每亩800元,那时,“已不怎么种粮了,开始种花卉。”
种地赚不到钱,种粮没有规模效应,这是农民转种经济作物或将土地流转出去的根本原因。
从整个成都看,人多地少的矛盾更显突出。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七分,“逃离农业”成为农村一景,部分耕种条件差的山区,甚至出现撂荒现象。2011年,崇州市农发局选择崇州3000户家庭进行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务农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跌到5%以下,有的家庭不足1%。更严峻的现实是,农村几乎找不到种地的年轻人。
“土地适度规模集中,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标志。”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说,减少农民数量,提高城镇化水平,关键要让农民带着“土地财产权”体面进城。从成都探索看,迈出的第一步是确权颁证,明确土地权属关系。
双流县兴隆镇瓦窑村,是成都2008年率先启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试点村之一。瓦窑村耕地、林地总计5000余亩,确权颁证前,村上每年9月根据家庭人口增减情况调整土地,俗称“分地”。一旦确权,将意味着“生不增、死不减”。村民对此争议不绝,更让村支书唐朝阳始料未及的是,村民提出:肚子里的小孩是否分地、承包面积与实际不符咋办、流转期限签多久?
越到细致的层面,意见越难统一。“我们不得不动用‘长老’、‘议员’,平衡各方利益。”唐朝阳说,各村民小组选举出一批德隆望尊的老人,代表村组村民协商解决问题。事后,成都将这个办法总结提升为“村民议事会”制度。
“一个问题,能激烈争论三天三夜,连在广州打工的都坐飞机赶回来参与,大家不断妥协让步,最后的方案让谁都无话可说。”从开始试点到拿到土地承包经营证,瓦窑村用了一年多时间。
随着2010年成都完成确权颁证,土地流转明显提速。瓦窑村3000多亩耕地,现在只剩下200多亩。该村议定的流转租金价格是水田每年每亩1000斤大米、旱地500斤大米、荒山荒坡300斤大米。
流转租金与地块的位置、出租年限密切相关。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网站发布的2013年12月出租信息显示,每亩每年租金从500斤大米到1300斤大米不等,租金最低的一块租期只有2年。
土地流转后,瓦窑村的多数村民成了“包租公”、“包租婆”,他们享有流转所带来的租金收入,以及附着在土地承包权上的耕保金及其它惠农补贴等财产性收入。唐朝阳的弟弟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跑到华阳做水电工,每月收入5000元以上,他的妻子就近在沙发厂工作,月收入也有4000多元。
总结瓦窑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精髓,唐朝阳用了一句朴素的话:“相信农民,就让他们自己来。”
“汤营模式”还活着吗
成都农业部门总结的流转模式,主要是从农民与规模化经营的关系和利益链接切入,在彭州土地银行模式、金堂业主租赁模式中,农民把土地承包经营权“预存”或是流转给集体经济组织,后者再进一步流转给企业。
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出现,使农民面对市场时有所“依靠”,减少了个体流转的风险;市场也有这方面的需求,搞农业项目讲求规模效应,不可能一户一户地找农民谈租地。与直接流转给项目业主相比,一些地方更愿意探索集体经济组织亲自“操盘”规模农业的模式,把农民直接变成经济组织的“股东”。
邛崃市羊安镇汤营村,是探路代表。
“单纯把土地租出去,落到每家每户头上的收益始终有限。”村党支部书记胡桂全回忆,汤营探索起于“眼红”。
2004年前后,一群浙江台州人到汤营村流转土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早熟西瓜,次年亩产效益让村民大吃一惊。“他们一亩收益3000元,我们收到的租金才800元。”胡桂全说,农民以前感觉种地是鸡肋,台州人吊起了村民从土地上挖“金元宝”的胃口。
他们找到村上,要求村集体组织带领大家一起搞项目,这直接推动了汤营农业有限公司的成立。
汤营模式的实质是,农民自愿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集体性质的农业公司,实行统一经营。这看似回到了“人民公社”时代,最大的不同却是,作为股东的汤营村民,享受“保底+分红”的待遇,每亩土地保底收入为800斤大米,公司经营净利润一半按股分红。
“8年间,汤营村农民的人均收入从4300元增长到1.3万元。”胡桂全算了一笔账:汤营公司主要吸纳当地农民参与项目生产经营,每年支付的劳务费200—300万元,分红近100万元。另外,农民不再种“应付田”,可以安心外出打工,又有一笔收入。
为此,《中国改革》杂志曾在2008年将“邛崃模式:农民分享土地流转收益”列入“2007‘中国十大改革探索’”。
不过,四川大学一位教授曾与胡桂全打赌,认为汤营模式很理想,但难以持续。汤营模式一开始就获得了邛崃市由国有投资公司入股的100万元风险资金,多少带有政府打造的色彩。而在两年间,公司规模持续扩大,入股土地1060亩变成2070亩,每亩800斤大米的“保底”并不低,生产成本高企。
羊安镇副镇长龚军说出另外一个原因:“以前是单家独户种地,现在是少数人种大家的地,最缺乏能够匹配现代农业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所以,那位教授一碰到兼任汤营公司董事长的胡桂全,就会半开玩笑地问:“胡书记,你还活着呢?”胡桂全向他坦陈,汤营村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局。
首先是缺少流动资金。“常规蔬菜的生产,算上农资费、人工费,每一季每亩需要1500元,2000亩就要300万元。”胡桂全说,尽管2009年后取消了保底,实行风险共担,但还是必须先投入才有产出,而且田间的轮作一茬接一茬,资金压力很大。
流动资金的缺口导致了一系列蝴蝶效应:产业难以走向高端,项目利润不高;村民“靠天吃饭”的观念,没有太大的改变。
虽然暂时没有亏损,但前路的阻隔已经看得足够清楚,汤营村民不得不面对“如何改变这个困局”。这两年来,村上逐步从经营产业向经营土地转变,目前已流转了1100多亩出去,公司自己经营的土地降至600亩。
换句话说,汤营村正过渡到大园区+小业主的模式。眼下,汤营村正与相邻的界碑村共同打造“生态羊安微田园”项目,围绕果蔬产业打造主题园区,发展乡村旅游。
胡桂全自己也承认,汤营公司能走过8年而“不死”,已是非常不易。
工商资本“下田”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时指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不能突破的“三条底线”:不能改变土地所有制,不能改变土地的用途,不能损害农民的基本权益。
这意味着,跃跃欲试的工商资本,流转农用地后,必须坚持姓“农”原则,耕地不能用于非农生产领域。据调查,成都土地流转主要用于水果、蔬菜、休闲观光、畜禽、农产品加工等产业。传统粮油种植,并不受工商资本青睐,他们更多的是关注设施农业、绿色有机农业以及都市观光农业。
“现代农业不再是买个种子施个肥那么简单。”成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朝林认为,现代农业的投入门槛高、科技水平强、回报周期长。
有机农业符合这种定义。目前,成都有202家企业从事有机农业,247个产品获得有机认证,认证耕种面积22万亩。但无利不起早,投资有机农业到底能否赚到钱?
“如果赚不到钱,那就不是做企业,而是做慈善事业,肯定不可持续。”上海多利集团董事长张同贵直言不讳。他在郫县租赁了2500亩土地,发展有机农业。“至少3年才能见效,要准备足够的钱,把产品做好;要准备足够的钱,建立消费者信任。”这是张同贵在上海的经验,上海项目前期仅4000亩土壤改良投入,就达到了6000万元。
在北京和耕农业总裁梅霖眼中,“三年”已经是很理想的投资回报期。这也是不少企业把资金投向农业领域的主因。但是,大量工商资本贸然进入农业领域,极有可能无法收获预期。
2013年11月8日,成都农业信息网刊登的青白江区农发局的调查报告称,该区“大部分进行农业生产的业主经营状况一般,除去生产成本后,基本持平。”报告分析,当地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较差,不适于连片种植和机械耕作,多数业主缺乏市场调研,风险不可控制,多数农产品在产地实行一级批发,同一种农产品在产出高峰销路困难。
不容忽视的是,进军农业的神秘面纱和各种期待被揭开后,不少流转企业感到流转成本过高;与此同时,农民又在抱怨价格太便宜,要求上涨流转经费。
新津牧歌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马丕,就正在经历这样的考验。该公司位于新津县华桥镇,一期占地800亩。“把生产设施、改良土壤的成本算进去,一亩地至少种出6000元才能保本。”马丕说,公司与农民的利益链接,是900斤大米,以及工作机会。出乎意料的是,公司聘请的农民,并没有多少积极性,“磨洋工”时有发生。农民对流转的意见也多起来。
马丕“得罪不起”。他试图调整流转租赁模式,找到农民协商,愿以每亩每年300斤大米的价格,“返租”给农民。“农民经培训合格后,负责生产,公司负责销售,并确定一定的比例用于分成,双方变成一个紧密联系的利益共同体。”马丕深刻体会到,农业企业要想健康发展,不能把农民抛在一边。
深水区羁绊
2013年中国土地流转探索,以一桩“丑闻”收尾。
山东枣庄市阴平镇银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邵长宝,身背1090亩土地流转抵押贷款,“跑路”了。
“跑路”事件产生的影响尚未可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会让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探索雪上加霜。融资难,依然扼住工商资本投入农业的咽喉。
早在2010年,成都出台办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作为抵押担保物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现实却是,银行不情愿,成功几率低,授信额度差。
2010年12月,成都市发生第一笔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崇州市隆兴镇杨柳村土地承包经营股份合作社,以101.27亩土地经营权作抵押,从成都农商银行获得16万元授信。这笔贷款与当地政府支持有关。
据成都市统筹委2012年4月的一份材料显示,当时全市经营权抵押贷款22宗,贷款287万元。2013年8月,被誉为“成都粮王”的邛崃固驿镇种粮大户周家林,终于在担保公司帮助下获得抵押贷款。“3000亩土地的经营权,仅获得70万元贷款,按照贷款额度不超过评估价值70%算,每亩评估价值不到300元。”周家林心里五味杂陈。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在高位法层面缺乏支撑是一大缺陷,成都出台的文件是地方法规,而银行又是垂直管理系统,国有商业银行自然不愿参与。
对于银行系统而言,一笔几亿元的贷款和一笔十几万元的贷款,所耗费的人力、精力、成本是差不多的,涉农贷款体量小、基数大,银行对庞大群体的掌握能力很弱,因此也带来了高风险。一位银行人士称:“毕竟经营权抵押只是作为有效的风险缓释措施,资金用途和第一还款能力才是关键要素。”
记者调查发现,已有不少农业企业因经营不善、资金短缺等原因退出。
此外,各界对工商资本涌入农村的动机存在争议。一派认为,社会资本投向农业领域,是支撑农业规模化发展、迈向现代农业的突破。另一派则认为,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其到农村大规模“圈地”,不仅会使粮食种植面积减少,还存在过度参与城镇建设的迹象。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担忧:“动则几千亩、几万亩的土地流转,一定与宣称建设什么公园、酒店、谋划什么旅游小镇有关,即使建设用地性质合规合法,是否会导致农业与第三产业发展本末倒置?”
在温江和盛镇友庆社区,几年间,已有几家流转企业倒闭退出,不过随着新的业主到来,并未发生租金纠纷。“流转企业需缴纳一年的租金作为抵押,他们的生产设施、花卉苗木等值钱的都在地上,农民才不担心他们‘跑路’呢!”吴建淡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