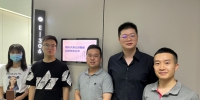国企改革新范式:制订国有股持有和股权行使政策
国企改革的新范式及政策挑战
新范式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推行主动性的、有时间表的总体性产权改革,以此为基础,推动公司治理转型和涵盖业务结构、资产负债、组织构架、管理流程、员工政策、薪酬福利、激励机制等在内的一揽子重组,从而实现企业的实质性再造和全球竞争力的重建。旧范式也包含产权改革的内容,但那在较大程度上是一种反应型、被动式的产权改革,过程是渐进的、进度是迟缓的,且经常摇摆不定。新范式产权改革,不应该等到越来越多国企陷入经营困境才去大规模实行,不应该采取得过且过、缺乏担当的机会主义态度,而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时间节点去设定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争取在2020年之前,使总体性的产权改革和一揽子重组得以基本完成。
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是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中实行名单政策,而不是分类政策和“一企一策”政策。这个名单完全覆盖各级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一级企业,即所有的一级企业都应该包括在这个名单中。在这个名单中,每个一级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名字和是否要实行混合所有制、实行混合所有制第一步的股权结构有什么样的限定。对于应该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级企业,每个企业都应该列明第一步的股权结构的限定。这个限定并不是把股权结构规定得一清二楚,实际上是要公布每一个一级企业大致的国有股比例限制。政府对每个一级企业规定了国有股的比例上限或者下限,就可以使国企自己,以及有意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社会资本,有一个清晰的政策界限。这比一个一个地去试探、去谈判要好得多。
无论未来国资管理构架做什么样的调整,都应该制订对混合所有制一级企业的国有股持有与权利行使政策。这个政策应该规定,一级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之后,国有股是由国资委还是其他哪个机构(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来持有。考虑到现实当中许多国有股的持有和股权行使是分开的,即国有股持有机构只是名义持有,并不真正行使股权,股权行使是由另一个机构来行使,或者通过另外的方式和渠道来行使,所以应该制订清晰的国有股权行使政策,以告诉外界,未来一级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之后,持股机构能否完整地行使股权,如果不能完整行使股权,哪些机构各行使什么权利,行使权利的渠道、方式、时间、触发机制是什么。还应该制订国资委和其他党政部门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政策(或者根据习惯叫做监管政策)。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上对深化国企改革有很大期待。当前,无论是在资本市场上,还是在实体经济领域,下一步国企改革的走向和具体举措都是一个受关注的议题。这里不妨谈一下国企改革的范式转变及政策挑战。
走出“旧范式”引入“新范式”
现在,许多人把关注点放在国企改革有关文件的出台上。笔者认为,新一轮国企改革,出台新文件很重要,引入新范式可能更重要。在过去三十多年国企改革过程中,各层面作了大量探索、实践、设计、调整,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改革轨迹,笔者将其概括为国企改革的中国范式。这种范式大致包括如下要点:第一,长期遵循实用主义思维,在很长时间里刻意回避产权改革,但不断推行激进的控制权改革;第二,长时间的激进控制权改革自发地走向渐进的产权改革,使产权改革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特性,导致国企改革较多地对内部人依赖和由内部人主导;第三,产权改革渐进地和摇摆不定地推进,具有机会主义特征和不确定性,并且与企业的业务、资产、债务重组交互进行;第四,很多母子型结构和集团化的国企选择碎片化的、各自突围的产权改革方式,即保留母公司的国有制不受触碰,子孙公司等下级法人实行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产权改革;第五,借助非国有企业崛起带来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国企改革,同时充分利用非国有企业崛起给国企产权改革和重组提供的缓冲作用;第六,激进的控制权改革和渐进的产权改革导致了巨大的企业改革成本,改革时间拖延之长又极大地增加了改革成本,对整个社会都构成一种代价,这种代价不仅体现在经济支付方面,也体现在公平正义方面。当然,这里对国企改革中国范式的概括不一定很完整,但应该涵盖了基本要点。这个范式是在曲折中形成的,是一个历史产物,在过去十几年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这个范式难以克服的种种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对产权改革的模糊性、摇摆性政策,其他很多问题都是由这一点衍生。国家在很长时期里本想回避产权改革,但为了避免产权改革,又往往以不断加码的控制权改革来作弥补,最后反而导致控制权改革失控,也导致自发的产权改革失控。对产权改革的模糊性、摇摆性态度和政策,在实际当中导致大量的碎片化产权改革,即国企不断分拆出子孙公司进行产权改革,看起来很多资产和业务被激活了或者分散突围了,但未实行产权改革的最上层母公司就成了旧机制的大本营和旧货仓库,集团性国企并不能真正实现市场化,反而因为碎片化的产权改革而使整体协同效应遭到削弱,一个集团内的子孙公司之间各行其是甚至打来打去,这就完全违反了国际上大企业集团的通用模式,即在母公司层面就解决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激励机制等问题并将效力一直贯穿到最基层的业务单位,而不需要由基层业务单位各行其是分散搞活从而破坏大集团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此外,还有计划经济遗产屡屡清理不净,或者清旧生新;资产、业务、债务的重组没完没了,重组成本此伏彼起,国企与政府之间的财务边界纠缠不清;公司治理软弱无力,且与来自于党政机构的监管犬牙交错,给中国国企构筑了全世界最复杂的监管体系但却仍然受到腐败多发和政商难分的困扰,等等。这种范式的最终结果,并没有使国企真正实现市场化,反而使国企在市场化和政策化、独立化和附属化之间不断拉扯、来去徘徊。
现在,当中国经济增长进入阶段性转折的时候,要使国企真正顺应“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一大趋势,就需要走出旧范式、引入新范式。
新范式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推行主动性的、有时间表的总体性产权改革,以此为基础,推动公司治理转型和涵盖业务结构、资产负债、组织构架、管理流程、员工政策、薪酬福利、激励机制等在内的一揽子重组,从而实现企业的实质性再造和全球竞争力的重建。旧范式也包含产权改革的内容,但那在较大程度上是一种反应型、被动式的产权改革,过程是渐进的、进度是迟缓的,且经常摇摆不定。新范式产权改革,不应该等到越来越多国企陷入经营困境才去大规模实行,不应该采取得过且过、缺乏担当的机会主义态度,而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时间节点去设定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争取在2020年之前,使总体性的产权改革和一揽子重组得以基本完成。
总体性的产权改革,重点对象是那些大型和特大型国企,特别是集团性国企的最上层母公司,包括央企的母公司。除了要改建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母公司之外,它们中的大多数应该实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相应的公司治理改造,极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国企可以保持国有全资状态,但也可试探多个国有机构持股的股权多元化。而对广大的中小型国企,可以实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多种放活政策。
在上述产权改革的同时,公司治理应该获得实质性转型,一揽子重组应该大力推进,使得大多数国企的业务结构更加合理、资产负债表更加健康、组织体系更加精炼灵便、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强化、三项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实现与市场接轨。这样的改革和重组如果能够得以实施,那些位居行业重要地位的大型特大型集团性国企将可以重建全球竞争力。
许多人会问,集团性国企的母公司,特别是集团性央企的母公司,具备总体性产权改革的条件吗?在当前情形下,母公司的产权改革和一揽子重组能推得动吗?事实上,不少集团性国企的业务、资产、人员状况基本上具备总体性改革的条件,一些集团性国企已经近乎实现了母公司整体上市,具备非上市方式产权改革的集团就更多了。即使那些资产质量不佳、经营状况不好、遗留问题很多的集团性国企,只要与一揽子重组结合起来,与下属 中小企业 的放活和综合性清理结合起来,仍然具备母公司产权改革的条件,其实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推行的债转股就可以作为大致的模板,现在缺乏的主要是决心而不是所谓的条件。极少数包袱特别重、人员特别多的国企,总体性产权改革和一揽子重组或许可以缓一缓,但外围清理有大量工作可做,外围清理得比较干净之后条件就差不多具备了。或者会有“算账先生”说,国有集团母公司的总体性产权改革和一揽子重组是很不划算的,那部分“好”的国有资产不能折成一个好价格,不能圈来更多的资金。这其实是一个不完全算账法,如果那部分“不好”的国有资产和相应的债务、包袱、遗留问题、旧机制不是留在母公司这个旧货仓库里而是一并解决掉了,那不就是省大钱了吗?看一看多年来那些似乎划算的改革吧,“好”资产圈来的钱还不是慢慢被存放的“不好”资产和债务、包袱、遗留问题、旧机制消耗掉了吗?也许还会有一种意见,认为对所有的国有企业,不管是集团母公司还是中小国企,只要实行与私营企业一视同仁的依法破产政策就行了吗?搞得好就继续搞,搞不好就依法破产,这不就是市场化了吗?为什么非得推行总体性产权改革呢?是的,一视同仁的依法破产制度的确是市场化,但这是一种被动的市场化,是等损失已经造成、经营难以为继时才来市场化。当然也不能否认这种被动的市场化对日常经营的市场化有倒逼作用,但重要的是,纯粹国有制和非市场机制是可以相互强化的,新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有很多论述,大量事实更可以印证这一点。
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实行名单政策
不过,引入新范式,需要克服一些不容忽视的政策挑战。
第一项重要的政策挑战,就是如何界定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企改革,要防止少数人大肆瓜分和掠夺国有资产,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是毫无疑义的。尽管在上一轮国企产权改革的时候,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和规章,以防止国资流失和腐败、防止各方合法权益受侵害,过去几年里还出台了更加细致的防止国资流失的各种技术性措施。但是,关于国有资产流失,仍然存在很多认知方面的分歧和法律方面的模糊地带。严格来说,国有资产流失目前还算不上是一个法律概念,但可以认为它接近于《物权法》第五十七条“低价转让、合谋私分、擅自担保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国有财产损失”的规定,以及《企业国有资产法》多个条款 “防止国有资产损失”的规定。《刑法》中也没有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一百六十九条中,规定“徇私舞弊,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或低价出售,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到底多少算是重大和特别重大损失,并不清楚。在实际当中,如何准确地判定国有资产流失,法律清晰度严重不够。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新一轮国企产权改革就难以稳健地、持续地、全面地推行下去。笔者认为,下一步迫切需要国家出台更加详尽的判断国有资产流失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可能会比较机械,但法律尺度很清楚,当事人只要遵循法律,就不必担心日后告旧状、翻旧账。
第二项重要的政策挑战,就是如何把握混合所有制的股权结构尺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把混合所有制提到了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样一个高度,但在实际工作中,就面临着股权结构和股份来源的选择问题。如果大部分国企,尤其是集团性国企的母公司,国家持有过高的股份,只引入一些股比较小的社会资本,不但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不足,也不利于公司治理的转型和经营机制的转换。因此,要推行新一轮产权改革,必须要有合适的、清晰的股权结构和股份来源政策,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殊非易事。
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是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中实行名单政策,而不是分类政策和“一企一策”政策。无论是“一企一策”,还是分类政策,理论上都没有错,因为每个企业本身就不是一样的,也是可以分成不同类别的,但在实际操作当中,“一企一策”的随意性太大,可能成为逃避改革、拖延改革的借口;分类政策可能在漫长的分类谈判和类别选择中掉入分类陷阱当中,最后改革的时机就耗费掉了。名单政策是确定国有企业是否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大致限定股权结构的政策。这个名单完全覆盖各级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一级企业,即所有的一级企业都应该包括在这个名单中。在这个名单中,每个一级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名字和是否要实行混合所有制、实行混合所有制第一步的股权结构有什么样的限定。当然,不实行混合所有制、继续保留国有独资的一级企业,只是少数,这少数企业保留国有独资,可能是因为它们将要被改建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可能是其所处的行业或所承担的功能比较特殊,也可能是因为历史包袱太重而且目前没有化解的方法。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名单都应该列明并且作出解释说明。而其他企业,争取在2020年之前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
对于应该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级企业,每个企业都应该列明第一步的股权结构的限定。这个限定并不是把股权结构规定得一清二楚,实际上是要公布每一个一级企业大致的国有股比例限制。政府对每个一级企业规定了国有股的比例上限或者下限,就可以使国企自己,以及有意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社会资本,有一个清晰的政策界限。这比一个一个地去试探、去谈判要好得多。同时,在整个名单政策中,政府应该就为什么对这个企业要设定这样的国有股比例限定作出解释说明。名单政策应该允许企业在股权结构限定的范围内,积极引入非国有的大股东,最好使非国有大股东单独持股33.4%以上或者与其他一致行动人共同持股33.4%以上,这样的股权结构才称得上实质性的混合所有制,通过上市等方式引入分散性非国有小股东只能勉强算是名义性的混合所有制。名单政策可以根据情况变化进行适时修订,修订的方向是不断降低国有股的比例限定,引导国有股份不断地释放给社会上的投资者。
或许会有一种疑虑:名单政策让国企对号入座,这会不会造成国企人心惶惶?以前的改革政府经常采取含糊策略,好像这样就能够避免人心惶惶,但事实并非如此,反而在私底下打听、议论和运作,尽量避免那些可能失去父爱依靠的“被改革”,这并不是好办法。其实,国外的那些大型国企的改革方案,涉时三年五年或八年十年,都是事先透明的,甚至是由议会通过的,只要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的正当利益得到保障,对号入座反而是最好的。
应该制订国有股的持有和股权行使政策
第三项政策挑战,就是如何确定国有股的持有和股权行使政策。由于大部分一级企业都要实行股权多元化或混合所有制,这些企业中的国有股由哪个机构来持有和行使股东权利,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不管国资委是否直接持有这些企业的国有股,国资委对这些企业以后如何管理,也必须纳入考虑范围。国资委直接持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国有股,没有实质性的法律障碍,事实上国资委作为出资人机构,本身就包含了持有国有股份的含义。所以,国资委可以直接持有混合所有制一级企业的国有股份,当然也不排斥以后由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来持有其他一级企业的股份(那时,现有的一级实际上已经变为二级企业,叫做二级企业更妥当)。这涉及未来国资管理构架的调整问题。
无论未来国资管理构架做什么样的调整,都应该制订对混合所有制一级企业的国有股持有与权利行使政策。这个政策应该规定,一级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之后,国有股是由国资委还是其他哪个机构(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来持有。考虑到现实当中许多国有股的持有和股权行使是分开的,即国有股持有机构只是名义持有,并不真正行使股权,股权行使是由另一个机构来行使,或者通过另外的方式和渠道来行使,所以应该制订清晰的国有股权行使政策,以告诉外界,未来一级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之后,持股机构能否完整地行使股权,如果不能完整行使股权,哪些机构各行使什么权利,行使权利的渠道、方式、时间、触发机制是什么。
还应该制订国资委和其他党政部门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政策(或者根据习惯叫做监管政策)。为什么需要制订这个政策?这个政策与对混合所有制一级企业的股权持有和权利行使政策有何不同?
照道理来说,哪一个机构持有国有股份,就由哪一个机构来行使国有股权,除此之外,无论国有控股还是国有参股企业,都不应该被其他任何别的机构进行股东权利之外的日常性“国有企业管理”或“国有资产管理”。这些企业也接受审计、透明度检查以及一些特殊行业的监管,但并不是针对国有企业、国有股份的日常性监管。但现实当中,不但这些被称为“监管”的力量仍然存在,而且更重要的管理力量是对国企“干部”的任免与管理。2014年,一些省市自治区出台的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当中,规定只要国有股份比例低于50%,国资委将不再按国有企业进行监管,这是一个进步。但是,难道国有股份比例高于50%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就应该接受国有股东权利之外的“监管”吗?这个“监管”是监管机构自己随时发个文件就可以去查、去指示、去审批吗?而且,也不光是国资委不再进行旧式监管就算数了,因为对国企高管人员进行“干部”管理的权限大部分并不在国资委手里,这涉及长期存在的“新三会”与“老三会”之间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涉及公司治理能否真正转型的问题。这些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第四项重要的政策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国企中残留的计划经济遗产。这就是所谓的处理国企的历史遗留问题。国企历史遗留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企业办社会,企业长期依赖为职工所提供的医疗、学校、后勤等服务;二是职工福利尚未或无法实行社会化,包括离退休职工的管理和统筹外费用、内退职工的各种费用、“三供一业”,等等;三是一些模糊地带,如国企职工身份的特殊性、国企的冗员较多又无法全部裁减,等等。国企的这些问题非常棘手,其实其中有些问题并不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东西,而是目前还在不断产生的新东西;甚至其中很多内容,譬如说一些所谓的办社会职能以及超统筹的福利待遇,也不能说都需要强制取消,但问题在于这些负债性的东西超出企业和企业股东的承受能力和承受意愿时,如何化解矛盾。这些问题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但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市场化,这些问题无法回避。因此,要推行新一轮国企改革,还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制订国企职工身份和相关权益、福利的解释政策,就像最高法院就一些重大而敏感问题作出解释是一样的道理,哪怕解释为各地区各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那也算是一种政策。国企职工已经成为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庞大群体,能否制订一个职工能接受、国家能承担、社会能平衡的政策套餐,以及能否使这样的政策套餐在实际中得以执行,实在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此外,对国企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基石中的作用如何认识,则是更深层次的挑战。这些挑战,都需要认真应对。
(来源:中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