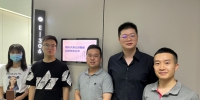美联储与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即将于今年1月底卸任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现在也许可以心情轻松地对自己说,他并未留给继任者一条迷雾重重的不测前路。在伯南克的领导下,美联储已于去年12月中旬宣布了其自今年伊始退出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的重大货币政策决定。按照事先预定的每月递减100亿美元的节奏,美联储将于今年内彻底退出已经实施了5年的三轮总金额超过4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
尽管1月10日发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显示去年12月美国的就业增长令人担忧地急剧放缓,但市场普遍预测,这一看起来疲弱的数据不会改变美联储既定的缩减购债基调和节奏。1月8日公布的去年12月美联储会议纪要清晰地表明,美联储官员近来对美国经济的看法明显转向乐观。他们对以“适度步伐”退出QE达成了强烈共识。眼下,他们越来越多地将关注重点聚焦于逐渐浮出水面的金融泡沫风险问题。
向来分歧重重的美联储内部对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表现出来的广泛支持,确保了候任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至少在就任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用不着为说服同事而耗费太多精力,这也可能是伯南克给予她的最后的一臂之力了。
作为伯南克的副手,耶伦一直是伯南克最坚定的支持者,这次也不例外。1月6日,在她出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的当天,耶伦对《时代》周刊描绘了她心目中的未来美国经济:“(虽然)经济复苏的速度之慢让人沮丧,但我们在降低失业方面仍然取得进展,预计通胀率将向2%的长期目标水准回升。”
拓展美联储的政策疆界
本·伯南克2006年接替被围绕在一片溢美之辞中的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就任美联储主席时,美国金融市场正在悄无声息地酝酿着一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作为一名研究大萧条的学术权威和当代最杰出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伯南克之前的所有学术努力都仿佛是冥冥之中在为他日后的使命做准备。
为了应对排山倒海而至的危机,伯南克带领美联储走上了一条敢于进取的非传统道路。过去几年来,只要认为有必要,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拓展美联储的政策疆界,扩大自己的职能。除了开动印钞机和将利率降低到零以外,他还曾一再坚定地表示,如果这些措施不再奏效,美联储还会有源源不断的进一步行动。
伯南克曾将自己任内的工作总结为最突出的两个措施:一是让美联储在2008年稳定金融体系,二是通过超低利率及资产购买拯救经济。在2012年底美联储100周年庆祝演说中,他并不谦虚地用“创新”二字来形容自己的“印钞”行动。他说,这种非典型的货币政策,拯救了摇摇欲坠的美国金融体系。
不论伯南克和美联储的救市行动的成效和结果究竟如何,在过去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联储看起来的确是华盛顿唯一的积极行动者。当其他部门由于政治纷争而被束缚住手脚,无法采取任何严肃行动时,孤军奋战的美联储简直成为了美国的最后希望。众所周知,自2011年以来,财政僵局一直拖累着美国经济的复苏。
同样让伯南克引以为傲的,是他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中央银行的传统行事风格,使得美联储变得更透明、更乐于同外界沟通。
早在伯南克还是一名教授的时候,他就对当时格林斯潘时代晦涩的“联储文学”表示出极大的不耐烦。他认为,货币政策当局应该传递明确的信息来引导投资者,而不是卖弄个人魅力,同时却将政策意图深深隐藏在云遮雾罩的费解语言中。
伯南克确立了美联储定期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并亲自主持,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伯南克的多年努力下,美联储于2012年初正式设定了2%的通胀目标;几乎与此同时,它还开始向社会发布利率预期。所谓“利率预期”,就是美联储对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一般是1年以上)内自己将要做出的利率决策的预估。伯南克显然希望利用这种“承诺”或“喊话”式的沟通更加直接地推动市场朝着有利于实现其政策目标的方向变动,当然,也有不少批评者质疑,这样的“预期”绑住了自己的手脚,压缩了政策的灵活空间,而一旦美联储预期出现差错,市场又会受到极大的干扰。
但伯南克已经通过大力推动这种“透明化”,在这家全球最重要的央行的货币政策管理方式上刻下了永久性的烙印。接替他的耶伦很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使用沟通这一工具,因为一直以来她都深信,沟通本身就是政策。
双重使命
我曾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今天的美联储被明确赋予保持货币稳定和实现充分就业的双重使命,但这其实只是一个新生事物(见《美联储“耶伦时代”帷幕或将拉开》,2013年11月25日《经济观察报》第38版);而且,这种双重使命放眼全球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最近一年来,日本央行一改以往的保守风气,在这方面表现得比美联储更为激进),欧洲央行(ECB)和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都只被赋予保持货币稳定的单一使命。顺便说一句,中国央行的政策使命由于其货币政策本身缺乏足够的独立性而难以界定。
自从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认为自己有责任使用宏观经济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减少失业。这一职责后来被编纂在1946年的就业法里,自那以后,增长和就业就取代了维护社会秩序和提供公共产品,成为评价以及选举政府的首要因素。一个未能交出令人满意的GDP和就业率分数的政府,就是一个不及格的政府。
但第一次明确地将实现充分就业纳入美联储职责范围的,是1978年通过的《汉弗莱·霍金斯法案》(Humphrey Hawkins Act),至今仅有30多年历史。作为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伯南克和耶伦都是这种双重使命的积极拥护者。从某种程度上说,身处金融危机中的他们对充分就业这项新任务可能比对稳定货币的传统任务看得更重。
然而,自《汉弗莱·霍金斯法案》颁布以来,一直有声音批评它不仅不可能达到目的(因为古典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与就业成高度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控制通胀与促进就业这两个目标是相互矛盾的),而且还严重削弱了自由市场体系,并在资本市场制造出一批痴迷于美联储政策的“瘾君子”投机者。在这些批评者看来,《汉弗莱·霍金斯法案》的实质,无非是国会为逃避做出艰难的——很可能是得罪选民的——政策决定而将美联储推到前台充当替罪羊,毕竟它的运转是高度独立的,没有选票的压力。
这些反对意见绝非毫无道理,在本次金融危机导致的衰退发生四年之后,在美联储几乎将货币政策适用到极限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速却仍然仅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衰退复苏速度的一半,美国的失业率也仍然居高不下。这就充分证明,美国的大部分问题或根本问题并不存在于货币领域,因而也非货币政策力所能及的。
虽然伯南克面向媒体和公众的公开发言中总是试图淡化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和“双刃剑”作用,这可以解释为是为了给民众和市场打气鼓劲儿,但在参加国会听证会和质询时,他曾经明确地提到过这一点。他说,美联储不能包揽一切,因为“支撑长期有力增长的大多数经济政策并不在央行的职权范围之内”。
这令比他更虔诚的凯恩斯主义者们大为不满,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在自己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专栏文章中将伯南克形容为一个懦夫。
利少弊多的红包
相比于美联储这种激进货币政策在激进复苏和减少失业两方面取得的微乎其微的收效,人们更担心的是它的严重副作用和后遗症,其中最一目了然的便是所谓“QE依赖症”——美联储的大规模印钞,让金融机构和企业对廉价资金产生了依赖。
随着一轮比一轮剂量更大的“印钞”猛药的投入,美联储再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美国式”的政府部门——一个躲在幕后的难以察觉的市场“规范者”。相反,它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主角,一根指挥棒。越到后来,美国金融市场越来越成为了投资者对美联储量化宽松推出或退出与否的押注,并因来自美联储的风吹草动而大起大落,相信这也是它招致信奉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哲学的共和党保守派者猛烈抨击的根源。
就拿伯南克一再试图推动和强化的市场沟通策略来说,如果他的意图完全实现了——投资市场真的亦步亦趋跟从政府的发令枪,在国债实际利率走势等各方面沿着政府希望的轨道前进,这对自由市场经济来说,真不知道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伯南克最激烈的批评者、美国众议院议员、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罗恩·保罗(Ron Paul)正确地质问道:为什么他们知道利率应该是1%,而不是3%?因为他们比市场更聪明吗?
这几年来,美联储就像一个在资本市场上派发红包的“圣诞老人”。只是圣诞老人虽然人见人爱,却只存在于童话中。许多人抱怨,美联储派发的这些红包对美国的实体经济有害无益,或者利少弊多。市场日益忙于解读伯南克说了些什么,而非来自实体经济的数据。去年5月,伯南克首次宣布美联储将会考虑逐步减少债券购买数量(也就是退出QE),一度引发了市场的剧烈动荡,尤其是股市,它完全无视强劲复苏的美国经济现实而出现暴跌。
那一轮美国金融市场的恐慌性波动稍后还伤及巴西、印度、印尼等新兴市场,在全球各地市场掀起巨浪。它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美国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已经多么离不开美联储这台“印钞机”,他们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它停下来。
于是,如何稳妥地退出QE而不对市场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本身便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一件头等大事和巨大难题。有经验的母亲都知道,给婴儿断奶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还有人甚至断言,即便美联储如期减少债券购买,乃至完全退出量化宽松,但是既然这种“创新”已经被制造出来了,就再也不会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生活里消失——市场永远都离不开美联储这根拐杖了。
对美联储权力的反思
2013年12月23日是美联储成立100周年的纪念日,一个世纪前的这一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签署《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标志着“中央银行”这一全新的经济和金融管理机构的诞生。
虽然经济学界和社会舆论对这一新政府机构的必要性和功能的质疑自它诞生那天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总体上说,100年来,美联储以及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的职权都在不断扩大之中。与政府介入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程度不断加深同步,它们在经济和市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令人略感意外的是,本次金融危机虽然也像以往一样进一步强化了美联储和全球各央行的权力,但却也触发了对它的广泛反思和强烈反弹。
政治观察家说,“在华盛顿,一半人想要杀杀美联储的威风,剩下的另一半人则想减轻它的工作。”这种政治空气的变化显然得到了民意的支持,彭博社(Bloomberg)于2011年底美国经济前景最为糟糕的时刻所作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的美国人希望削减美联储的权力,其中不乏支持废除它的人。
我不知道这种观点会不会得到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支持,大概没有什么人比这位名满天下的经济学泰斗对货币政策有更深湛的研究了。但就我所知,恰恰是这位创立了货币主义学说的伟大经济学家,毕生都强烈反对赋予中央银行过于强大和独立于议会监督的权力。他曾在《货币稳定方案》一文中提出建议,将美联储降低为国会推行其货币政策时的一个具体执行部门,性质上类似于财政部,从而大幅削减它自行处理货币事务的权力。按照弗里德曼的方案,就连国会本身,在决定货币政策时也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依据一套标准基本固定的公式。
但在另一方面,弗里德曼对大萧条的研究结果似乎又是倾向于支持伯南克的货币政策的。他通过自己独树一帜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结论说,上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萧条”并非一般认为的“市场失灵”所致,亦同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根本扯不上关系。相反,正是成立不久的联邦储备系统的致命错误——在应该放松的时候反而收紧货币,进而听任大量银行破产倒闭——造成的连锁反应,使得一次原本应该影响有限的小型经济衰退急剧扩大和蔓延,最终酿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并最终触发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全方位灾难。
回归传统
那些支持“废除美联储”的人士的理由是:作为一个新的强大的市场参与者,美联储本身已成为一个不健康的干扰,使人们难以专注于改善自由市场体系或展开更为根本性的经济政策辩论。他们振振有词地指出,相比1913年之前,美国政府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大大加强,采取所谓“反经济周期”的举措以稳定经济的政策例子也很多。然而,事实上这100年来的美国经济表现得比上100年更糟,而不是更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破坏经济稳定的首要罪魁正是美联储本身。
这给保守派政客的政治主张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前文提到过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恩·保罗两年前曾出过一本名为《终结美联储》(End the Fed)的书,将30年代的大萧条、60年代的黄金储备骤减、70年代的滞涨、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以及当前的这次危机和衰退都归咎于美联储的错误政策。
虽说罗恩·保罗们的主张有些极端,但他们的有些见解依然是值得认真倾听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似乎已经抛弃了储蓄和投资是真实财富和经济增长来源的观点。政策制定者致力于刺激消费,却忽视了生产。这些所谓的资本主义者忘记了资本不可能通过政府指令来创造。
因此,近年来,一直有保守派共和党议员致力于推动立法,将美联储的职能重新收缩到“维持物价及美元币值稳定”这一单一使命上来。就连一部分现任美联储官员自己也开始支持上述观点,圣路易斯联储行长詹姆士·布拉德(James Bullard)就曾公开表示过:“(美联储)承担单一使命已经够了”。
在21世纪的今天,当相信美联储的权力“神授”的人越来越少之时,它也许会尴尬地发现,自己的首要任务是竭力证明美国经济在有它的时候比没有它的时候要更好。过去6年来,伯南克的大胆举动背后的动力大概就在于此。
100年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的衰落、冷战和美国单极体系的确立,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也经历了英镑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金本位制的瓦解以及美元体系的奠定。在下一个100年里,美联储也许不会被废除,它还将面对许多更大的未知。
然而在当下,它最应该做的,恰恰是回归传统——帮助(而非阻碍)美国实现重大的经济转型,即转变成为一个由储户组成的经济体,而不是一个完全依赖那些过度举债的消费者的经济体。这就需要美联储回归政府机构的本分,而不是去助长金融体系中的病态行为。
如果珍妮·特耶伦想要带领美联储平安地度过“后金融危机时代”和“后伯南克时代”,她应该经常自问的一个问题是:你看到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吗?